醫生,笑一笑
我請患糖尿病的年輕女病人到手術室去,切除大腿。她看不見從足到踝而且快要蔓延到身體其他部分的那一大片黑色潰瘍。因為她兩眼也瞎了。足部綻開的腐肉像三角洲氾濫,支流正向足趾伸展。她雖然看不見潰瘍,卻感到痛楚。無血的肢體腐爛化膿,是最難受的。
過去一年多,我不時為她割去腐肉,清潔足部敷藥裹傷,設法阻止潰瘍惡化。她每星期三次坐在我的手術台上搖來搖去,在黑暗中伸出腿,但把大腿當作必須保持穩定的火箭緊緊抓著,唯恐一時不慎便會炸開她的足趾,令碎肉散佈全室。我割去一片瘀藍的腫脹皮肉,這裡割一點,那裡割一點,割下來的都是她的血肉。
我們終於放棄了,她和我。兩人的努力再也趕不上壞疽擴大的速度。腿腐爛的那麼厲害,再不切除她便沒有命了------我或許也活不下去了。我要拿起刀鋸,切去腐腿,我們才可以痊癒。
今天是動手術的日子,麻醉師施麻藥時,我站在一旁,看見那熟識而又緊張的身體鬆弛下來,漸漸入睡。然後我掀開蓋著她大腿的布。
就在她膝蓋上,她倒畫了個臉給我看:那只是一個圓圈,兩隻耳朵,兩隻眼睛,一個鼻子和一個笑得上翹的嘴。下面她用正楷寫著,醫生,笑一笑。幾分鐘後,我聽到鋸的聲音。最後突然一聲,告訴我腿切斷了。
學者
加強護理病房裡躺著位飽學之士。他是教授,習慣研究文字,教導學生。一天,他在教室內講授美國女詩人狄金蓀,忽然臉色灰白,露出訝異神情,彷彿初次看見和明白他有生以來從不知道的一樣東西。那是受創的樣子,在身體深處看不見的地方,受到無聲的打擊。學生們不知道就在那時他的胃壁穿了,胃裡的東西正像四面搶掠的群鬼湧入腹膜腔。
他從黑板前搖搖擺擺地轉到書桌前,倒在桌上,臉側向一旁,吐血,一大口一大口的血塊,好像把所有的精神獻給學生之後,還要獻上血和肉。
不久他被送到手術室去。我認識他,他教我念過詩。我雙手抱起他,切開他的身體,我尋出血部分。我縫上裂口,敷裹傷處,然後說:「你現在好了。」
但事實並不好,他要死了。儘管我全心全意挽救他,也不能把他拉回來。我們把他從手術室送到加強護理病房去。他的家人和學生來到電子門外便要止步。他們不能進去,因為他進入了新境界,到了他們不能去的接待室。
三星期以來,他一直住在加強護理病房裡,刺了許多針孔,身上的竅口插滿了大大小小的管:用來注洗傷口,濾膜分析,吹空氣入體內,抽水分,排出膿水......他感受到每個針刺和每一下壓力,就像熱戀的人,愛火冒到皮膚上一樣。
室內有一位穿白衣的婦人在走動。她滿懷愛心量度他每小時排出的尿。她雙手熟練地把氧泵入他的鼻孔,默數著他的脈搏。他的體力每次弱一點,她都哀傷地搖搖頭記下來。最後她不再用機器,親手去感覺,然後歎了口氣,扯下被單,冼淨他的四肢。
飽學之士從來不認識這婦人。他全神貫注地迎接死神,簡直不知道她就在跟前。可是在他接近死亡的新階段中,護士就是他的妻子。兩人很親密。這一次結合,儘管二人並沒有分享過去的日子,卻共同佔有眼前這段可怕而緊張的時光。現在這次結合把他們密切地聯繫在一起,聯繫得比任何諾言更緊。
沒有人知道自己最後的氣息要從誰的手中溜去。只為這一點,我們就應該對陌生人更加仁慈。
與神相會
我站在少婦的病榻旁。她的臉動過手術後,嘴巴部分的肌肉癱瘓,歪扭得像小丑的表情一樣。連接嘴巴的一小段面部神經割去了。從今以後,她永遠都會是這樣子。外科醫生已經盡量順著她面部肌肉去做手術了,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可是為了移去她面頰的腫瘤,我不得不切去她那小段神經。
她年輕的丈夫也在病房內,就站在病床另一旁。兩人在黃昏的燈光下好像跟我隔離,而在互訴衷曲。我自問:這兩個毫不顧忌,這樣貪婪地看著對方、接觸對方的人,那個他和那個被我弄成那麼歪扭的婦女,到底是什麼關係?少婦先說話了。
「我的嘴永遠都會是這樣子?」她問道。
「不錯,」我說,「永遠是這樣子,因為神經切掉了」
她點頭不語。可是男子微笑著。
「我喜歡這樣子,」他說,「玲瓏。」
我立刻知道他是誰。我明白,不敢再仰視他。凡人沒有面對神的勇氣。他毫不介意我在場,低頭去吻她歪扭的嘴。我站得那麼近,看見他也扭曲自己的嘴唇去配合妻子的唇型。表示兩人還可以吻得很好。
我記得古希臘的神化身為人,出現在塵世上。我憋著氣,只覺得不可思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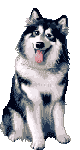
Title :美麗的化身
Author :理查德.塞爾澤
|